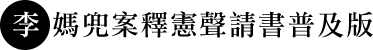
擔任中共「臺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的李媽兜,如果活躍在當今臺灣,大概就是一位崇尚共產主義,對組織運動熱血積極的中年大叔。但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李媽兜這樣「貨真價實的匪諜」,除了統治者亟欲除之去而後快,也不見容於當時有效的法律規範。
在那個年代,如果有人「打算」破壞國家體制,用不正當的方式占據國土,或者採取行動,非法改變憲政體制、推翻政府,便會遭到國家以當時有效的舊刑法第一百條加以制裁。[註1]舊刑法第一百條原本罪不至死,然而,一九四九年通過的《懲治叛亂條例》加重處罰,導致觸犯舊刑法第一百條變成唯一死刑。[註2]《懲治叛亂條例》除了加重刑法規定之外,還規定在戒嚴區域內,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的人,無論是否具有軍人身分,一律交由軍事機關審判。
李媽兜落網之後,保安司令部以他到處吸收成員,建立共黨地下組織的行為,觸犯舊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為理由,將李媽兜交付軍法審判。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保安司令部判處李媽兜死刑。[註3]同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六點,在今天臺北中正橋南端的刑場執行槍決。
*
一九九〇年代,政府當局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開始處理過去國家暴力造成的人權侵害和不正義。在立法層面上,立法院先在一九九二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這是臺灣首部轉型正義法律。接著又在一九九八年,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在戒嚴時期受到不當審判的受刑人,在解嚴之後可以透過戒嚴時期補償條例申請補償。然而,補償條例也限制了補償資格。舉例而言,審查補償申請案件時,如果透過目前有效法律規定的證據法則,確實能證明被告觸犯內亂外患罪,那麼受裁判者或其家屬不可以申請補償。[註4]生錯時代的李媽兜,肉身承受了巨大且不可回復的國家暴力,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仍然無法賦予他任何補償或平反機會。
臺灣的轉型正義,目前仍以補償為主。在落實的過程中,如同李媽兜這樣因為法律規定而受到限制的情形,也發生在許多中共地下組織工作者的身上。而一九九二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使得所有戒嚴時期相關案件在民主化後無法上訴或抗告,只能透過再審和非常上訴救濟。[註5]這樣的規定降低了臺灣經由司法落實轉型正義的可能性。此外,大法官在釋字第二七二號中,認為國安法有關不得上訴或抗告的條文合憲,更成為臺灣社會難以從司法面向落實轉型正義的阻礙。至於先前提過的舊刑法第一百條,除了在戒嚴時期壓迫異議人士之外,也是民主化之後實際上阻撓受裁判者申請補償的法律規範。即使《懲治叛亂條例》已經在一九九一年廢除,刑法第一百條也在一九九二年立法修正,卻因為是「判決時的有效法律」,持續在這些政治案件上發揮超越時空的作用。
這些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違反了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共同接受的價值,正是本件聲請書主打的對象:
1.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的補償基金會
負責審理補償申請的是「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然而,由內政部委託處理業務的補償基金會,透過「決定」行使公權力(行政權),判斷過去法院判決是否不當(司法權),已經違反憲法要求的權力分立原則。
2.未能落實憲法核心價值的補償條例
轉型正義的目標之一是「對於過去國家整體不法的反省」,但是補償條例有意排除某些戒嚴時期觸犯內亂、外患罪「確有實據」的案件,恐怕不符合轉型正義的精神。此外,轉型正義的另一個目標是回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大法官也曾在釋字第四九九號中肯定這樣的秩序為我國憲法核心價值。補償條例不僅簡化轉型正義的目標,也未能落實憲法的核心價值。
立法者透過戒嚴時期補償條例與國安法,選擇放棄司法訴追程序,將重心放在金錢補償,體現出臺灣過往轉型正義的不足。
1.違反憲法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
有很多違法行為,在動用到補償之前,其實有許多排除侵害,使權利回復原狀的可能。例如,土地遭國防部不法占用、財產遭沒收尚未返還或名譽遭減損未予以回復名譽等等,這些都應該搭配補償之外的其他救濟手段,供受害者選擇。補償只是許多救濟手段中的一種而已,在法律術語中,我們稱呼補償為「第二次權利保障」,人民因為國家違法行為,導致權利受到不可回復損害的「事後賠償」。對於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的當事人而言,在法制層面上,多種救濟選擇可能性,例如,給予完整的上訴權平反案件、申請回復被害人名譽、申請返還遭沒收的財產等等均付之闕如,甚至因為國安法而限縮現有的救濟管道,這樣的立法顯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2.幾乎沒有救濟可行性的國安法
就救濟的可行性來說,如果真的依照《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的方式提起再審和非常上訴,我們會發現,這些訴訟途徑對於平反舊案根本毫無幫助。
首先,《刑事訴訟法》上的再審,要求以「新事實、新證據」開啟程序,但是,大多數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都存在「證據偏在」的問題,也就是大多數證據與資料都掌握在國防部手中。如果國防部不公開,受害者及其家屬根本不可能尋得任何打開再審程序的新事實與新證據。
此外,《刑事訴訟法》設計非常上訴的目的本來就與人權保障較無關係。一般來說,所謂的非常上訴,其實是為了統一解釋法令,至於當事人的權利救濟,並不是主要考量(相關規定可參照《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七條、第四四八條)。
釋字第二七二號認為國安法合憲的理由在於,該條條文捍衛了法安定性。[註9]法安定性是法治國原則(rule of law)的重要內涵,政府要獲得人民信任,讓民眾願意遵守法律的前提之一是法律規範穩定且「能夠預測」,不能無緣無故地朝令夕改讓人民無所適從。[註10]
然而,轉型正義要處理與克服的對象,幾乎都存在著法安定性和正義的衝突,這個難題並不僅止於政治案件。解嚴至今已將近三十年,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也作成二十餘年,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卻因為證據資料均為國家所掌握,適用的刑法條文晚至一九九二年後才修正,使得當事人難以循再審與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對於渴望透過司法平反的當事人而言,這些現有能夠選擇的「救濟」規定,如同畫餅充飢。
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並未成就「同時兼顧法安定性與權利保障」的目標,更未考量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的特殊性,最後只捍衛了「不法」判決的安定,強化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的合法性。
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應重新審理,以重建憲法要求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透過這個過程,重新評價非常時期國家種種的權利侵害行為。基於這個理由,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應加以補充或變更解釋。
立法院確實已經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並且修正舊刑法第一百條。然而,補償條例「不得申請補償」的法律效果 ,依然與《懲治叛亂條例》和舊刑法第一百條互有因果關係,在判定當事人或當事人家屬是否能申請補償這件事上,成為實際上阻擋受害者申請補償的法律規定。換句話說,這兩個在戒嚴時期危害人權最嚴重的「政治刑法」,仍然能在民主化後的臺灣發揮作用。因此,在檢討補償條例「不得申請補償」是否違憲之前,也應該回頭好好檢驗《懲治叛亂條例》和舊刑法第一百條的合憲性。
[註1]《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第一項)
前項之預備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
[註2]也就是俗稱「二條一」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註3]保安司令部(42)安度字第○二○二號判決。
[註4]《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償……二、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
[註5]《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於解嚴後依左列規定處理:……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
[註6]此部分涉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註7]此部分涉及《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
[註8]此部分涉及大法官釋字第二七二號。
[註9]「為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
[註10]法安定性原則的內涵還包括法明確性原則、不溯及既往原則和信賴保護原則等。
[註11]此部分涉及《懲治叛亂條例》和舊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
[註12]參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